锄头之美
如果单纯从审美的角度去考量,锄头在诸多农具中绝对没有形态上的优势,那笔直结实的木柄与宽大锋利的锄刃组合在一起,尽管非常经久耐用,却总是靠在门背后,或者躲在旮旯里,一幅木讷耿直的模样,入眼就能让人蓦地想起我那不善言辞的父老乡亲。而在文人墨客的眼里,这锄头似乎至臻至美:"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赞颂的是劳动之美;"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抒发的是恬淡之美;"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描述的是闲适之美……
事实上,锄头的最妙之处在于轻便,在于实用。它不像犁铧那样需要耕牛进行主导,不像镰刀那样需要刈者躬下腰身,它被农夫紧紧握在结满老茧的手中,既可除草、作垄、耕垦、盖土,亦能中耕、碎土、挖穴、收获,并且水田旱地通吃,散文家梁永刚称其为农具家族中的"大拿".这种比喻虽然比较新奇,也很接地气,但我更愿意将锄头比作农夫的一条胳膊或者一位伴侣,因为从春到秋,跨夏至冬,它与主人几乎是不卑不亢地形影相随,是有礼有节地相濡以沫;尤其是草木葱茏、花卉绽蕊的季节,锄头在农夫的双手有规律地运作下,于杂草丛生的垄亩之间恣意游走,随到之处,无不披荆斩棘,那"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气势,与手握镰刀努力刈割的快乐场景相比,真的有过之而无不及。
别以为锄地仅仅只是个体力活,它与唱戏一样也是门艺术,特别讲究"手、眼、身、法、步"的综合运用。老把式锄地,在手法上非常注重"一步一换手",也就是左右开弓,这样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或者往后倒退,不仅有章有法,而且质量很高;在眼法上要聚精会神,一锄下去,绝对保证去掉的是杂草,留下的是禾苗;身法则以个人喜欢的姿势而定,一般不能将腰板躬得太深或将腰杆挺得太直,这两种姿势都很容易使人劳累;当然,步法的作用也不可小觑,锄地之时,脚步的挪移重在"一步一个脚印",一垄到头,回望那一行踩出来的脚窝,就像是雪地里留下的整齐规则的脚印,乡亲们形象地称之为:开在泥土上的"脚花".
从表面上看,这"脚花"是锄地艺术的衍生,既赏心悦目,又独出机杼;深层次探究,它可是辛勤汗水的结晶,是劳动经验的淬炼。《农政全书》对此有所总结:"锄法有四:一次曰镞,二次曰布,三次曰拥,四次曰复。"我的父老乡亲对这"四法"肯定讳莫如深,但是绝对深谙其中道理,因为他们亘古至今都把大地当作自己施展才华的舞台,因为几千年的耕作传统告诉世人:好锄头与好农夫为伍,如同良田碰到犍牛,伯夷遇到子期,是好知音,好搭档;只有这般绝配,才能达到锄地时的游刃有余,才能取得劳作上的心手合一。
既然能与锄头融为一体,那么这锄头也就有了生命,有了灵魂。它明亮或者生锈,都能从一个侧面映照出农夫的勤劳与懒惰——勤劳的人,锄杆是润滑的,锄板是明亮的,庄稼地是葱茏的;懒惰的人,锄杆是粗慥的,锄板是上锈的,庄稼地是荒芜的。如此两厢比较,这锄头就成了一把笔直的尺子,始终在丈量着从村庄到田畴,到底要迈出多少坚毅的步伐;就仿佛一根高耸的标杆,时刻在昭示着从春播到秋收,到底要刨出多少生活的希望。
乡亲们常说:只有紧握锄头,才有五谷杂粮,才能心里不慌。遗憾的是,远离乡村的我已有多年不知稼穑之累,不晓耕耘之苦;即使在电视或电影中偶尔见到那锋利的锄头,也是置若罔闻,或者漠然视之。不过也有欣喜的地方,因为每每坐在桌前,我总认为手中的那支钢笔就是一柄缩小版的锄头,尽管现在很少用它在方格田里"刨食",但是只要郑重其事地写下一字一句,我就觉得自己与所有的父老乡亲一样,敬重锄头就是敬重粮食,感恩锄头就是感恩土地!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笑语山歌里,和风丽日下,感受着浓郁的田园气息,我多么向往挥舞锄头,种出瓜果遍地,种出五谷飘香,种出满目青黛,种出人生精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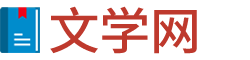 返回首页
返回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