槐米,慢点儿落
每天都要经过这里,见到这些槐树,老家人叫它黑槐,开的花叫槐米,果实叫槐豆。
只不过,家乡的黑槐是野生的,长在沟里,没人收拾,只会疯长,胳膊粗的枝条会被父亲做成锨把儿。城里的槐树,被人修修剪剪,当成花木打理。
马路边的槐树,围着成片的居民楼,聆听着城市里昼夜不息的声音。老家的槐树,与其他杂木混在一起,经风历雨,任鸟雀喧闹。
家乡有了那些树,便有了乡村的气质。城市有了这些树,才有城市的生机。
初春的天气,乍暖还寒。终于到了春日迟迟的日子,槐树发芽了,淡淡的浅绿、明黄,在枝丫上慢慢舒展,像迎春花开了满枝。这样的情景让我暗暗吃惊。记得那时春天里,年少的我随父亲在沟底放羊,那些张牙舞爪的树,何曾这样令人惊艳过?
初夏,槐树的绿色最纯粹,水洗过一般,崭新而娇嫩。起风了,风撵着这些绿,从路南到路北,从路东到路西,像记忆中老家的涧水,缓缓地流啊,淌啊,从心里流淌到梦里。
盛夏来临,树冠越发蓬松,像妇女高耸的头发,它们拱在一起,把路变成一条绿色的隧道。太阳很大,却被这些绿融化了,阳光碎了一地,像涧河上闪烁的波纹,更像母亲眼里的点点泪花。
我喜欢秋天,因为秋天是收获的季节。这些槐米要不了多久,就会长成槐豆。
立秋前一天,我回老家。父亲突然问我:“你们那儿的树,槐米稠吗?”我说:“那些槐米只有小米粒儿大小,采摘还得等几天。”其实,那一串串、一穗穗槐米已经咧开了嘴儿,香味几乎消失殆尽了。早年,父亲会把槐米或槐豆摘了晒干,母亲会把槐米和小米放在一起,用砂锅熬成粥,清凉败火;槐豆可以泡茶,利咽清肺。现在,家里飘出的不是粥香或茶香,而是中药的清苦味道,那味道无声无息,却时刻萦绕在我心头。
父亲居然还惦记着这些。我告诉他:“今年雨水足,槐米开了很多。”父亲想了一下,试探着说:“等我好了……咱们去摘。”我说好。父亲接着又说:“涧河涨水了。”我问:“是吗?”他紧接着问我:“你还记不记得,那年我驮着你去看涨水?”怎么能忘记呢?那年,我五岁。
那年涨水,全村的人都站在沟沿看稀罕。水头来势凶猛,浊浪滚滚冲击着堤岸,河边的树木东倒西歪。父亲紧紧把我搂在怀里,嘴上却说:“丫丫,把你扔河里冲走吧?”我搂着父亲的脖子,拧着父亲的鼻子说:“你才舍不得。”父亲问为啥,我说:“你只有我一个闺女啊。”
时隔三十几年,因为中风脑子不太管用的父亲,却记起了这件事,说起当年我的“刁蛮”。他边说边笑,笑了两眼泪。我也笑,只不过那眼泪,流在我心里。
我不想对父亲说,路上的槐叶三三两两已经黄了,要不了多久,就会叶落枝空。我多么希望今年的秋天能慢点儿来,还有那些槐米,能慢点儿落,慢点儿结荚成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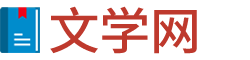 返回首页
返回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