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爷
清明去祖上添土,乡野枯蒿间,二爷的坟头显得尤为瘦小,多像二爷在世时的个头,不经意的存在着。风唐突的吹过,卷起一抹黄土,旋幻成二爷清瘦土色的面容……
二爷一世未娶,半生给了国家,半生给了家族。徐州会战时,二爷和村里几个壮年去前线支援。枪林弹雨中,二爷用竹子做成担架,一遍遍穿梭在战火中,来来回回运送伤员。战争结束以后,部队统计人员,叫二爷报上名字,二爷随口说了个假名,问住址,二爷又隐瞒。组织上给每人发了一张小纸条,二爷也有。哪知二爷不识字,半道给扔了。再后来,政府发放补贴,和他一块参加革命的都有保障,二爷因当时统计时报了个假名,这假名是他随口编造,二爷也记不起来了,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享受。二弟上大学时,当地组织上也确实来我家核实过此事,叫二爷去找些当时的证人,补齐材料,二爷却是呵呵一笑,终究没有迈开腿去走动。以后,此事再未听二爷提及。
功名利禄,如二爷上衣口袋里的烟盒纸,随手这么一扔,熔在了岁月的炽汁里。
生产队没解散时,二爷在老牛棚喂着牲口,吃住都和牲口在一起。二爷用他那结满茧子的手,一手抓抓牛粪蛋,一手又抓抓饭缸子。队里的牛个个膘肥体壮,赶得过二爷的体格。拉起犁耙,走起碾磙,一天一夜不知疲倦。二爷把牲口照料得如此精细,却忘了自己的“老本”,一次得了“浮肿”,浑身有气无力,差点断了性命。队长念二爷是有功的人,拉到伙房上不按公分的吃住,半月有余,二爷才算站了起来。
我记事时,二爷已是老头样了:焦黄的脸皮渗透着横七竖八的条纹,瘦瘦的,矮矮的个头,终年一身黑旧的粗布衣,上衣的纽扣从没见他扣住过。走路时一只手腋着门襟,一只手左右摆动,脚下虎虎生风。说起话来亮亮堂堂,如当年打鬼子时吹响的军号。
二爷床底下放着根扁担,二爷用它一头挑针头线脑,一头挂弹弓渔具。二爷挑起扁担,风里来雨里去的走南跨北,四下里吆喝度营生。二爷挑一天的担,走一天的路,常常回到家累得倒头就睡,有时母亲熬好了汤叫我给二爷送去,往往脚尖踏进二爷的门槛时,二爷已打起了鼾声。
二爷有一回下乡回来得晚,半道遇一个走亲戚的老太太,因天黑看不清路,连人带行李翻进了沟里。时值腊月天,老太太甚是绝望。双手拼命的在冷水里挣扎。二爷顾不得挽脚口,扁担一撂,跳下水去,连扯带拉的费尽了气力,硬把老太太拽上了岸。老太太冻得坐在路边哭,二爷又跑到家院,拉了架子车,架车上铺着二爷的被褥,二爷一路小跑,把老太太送到了她家,等老太太见到她儿子时,二爷已累得满头大汗,黑棉袄贴住了脊背。老太太家人跪下就给二爷磕头,执意要给二爷些财礼,二爷果断的拒绝了。出了大门,二爷拉起架子车,摸着黑路,一鼓作气赶回了家。
庄里人多有不厚道的,背地里调侃二爷傻,二爷听到风声,往往也是呵呵一笑了事。
我和兄弟读书时,家境正贫。父亲常年在外打零工,母亲在家收拾几亩薄田,喂着一群羊。田间农活虽累些,倒也好收拾,但这羊群却不好带,赶上雨季,叫得十分烦人,每天夜里时不时的还要添些草料,我和兄弟放了学就要牵到地里放。最麻烦的是,母羊到了分娩日,尤其费心。幼羊若脑袋先出母体,便也好受,那是顺产,多半顺利。若赶上后蹄先出界,就要麻烦,母羊叫的声也凄惨。还有横位生,羊羔子手脚往外,脑袋憋在母羊体内,这种状况,不是幼羊死,就是大羊亡。母亲遇此事,也常常手忙脚乱,使不上计策。这时,我们兄弟总会一溜风似的去后院请二爷,二爷喂了大半辈子牲口,对于牲口产崽护理了如指掌。二爷听到我和兄弟喊他,忙放下手里的碗筷,跟着我们跑过来。二爷一来,大小羊命算有了保障。二爷抓把麦秸垫在母羊屁股下,取半盆熟水净了净手,点了支烟燃上。
母羊大势是憋不住了,嘴里不住的打哼哼,一会卧倒,一会又站起,拧着绳子来回转。说话间,一个白团从母羊的体内跳跃出半个身子,小家伙奋力地挣扎着,一个劲往外蹭。二爷一个健步上前,稳稳地拖住羊崽的头部,缓缓的拉扯它的身躯,小家伙像做了个滑溜的梦,稀里糊涂的就脱离了母体,站在了麦秸秆上,浑身湿漉漉的,嚷着要吃奶了……
母羊产崽后,通常要忙活一夜不寐,羊也不睡,人也不睡,中间要给母羊清理恶露,扶起小羊教它吮吸奶头,还要当心母羊起身时,别踩坏了幼崽……
二爷陪在羊房里,忙碌了一夜,眼睛都熬成了乌黑色。
二爷喜欢牲口。二爷有时候会说,人和牲口是一样的,都有感情,只不过人能讲话,牲口不会说罢了。
记忆里的二爷,爱憎分明,黑白有度。遇见好人,二爷也是柔肠子,帮起忙来恨不能掏心取肺。若是哪个混蛋敢在他面前耍赖,二爷眼珠子一瞪,掂菜刀、拎板凳、横竖一个“倔”。
村头邱寡妇,蛮横不讲理,她家的田埂和二爷的地埂搭界。邱寡妇贪心,每年秋播之际,偷偷的把地埂线往二爷田里挪二尺,她以为二爷觉察不到。耩麦时,二爷负责摇耧。二爷种了一辈子的田,哪一块田耩多少垄麦,上下不会错半个耧齿。二爷见田地“蒸发”厉害,遂叫来了邱氏家人,当着大家的面,大软尺一拉,这下倒好,二爷种的田地整整跑进了邱家一丈多。二爷叫邱寡妇站出来解释,那婆子非但不脸红,反倒骂起二爷,二爷那次是真怒了,从腰间抽出了竹刀,忽闪一下,差点削到邱寡妇的鼻梁。若不是族人拦住,弄不好出乱子,二爷断不会罢休。二爷一刀下去,手腕子粗细的臭椿树拦腰两截。那邱寡妇斜着眼瞅了,吓得不敢着声,踮起小脚,啰里啰嗦地朝村里跑。二爷就在她背后使骂:“老子鬼子土匪都敢打,还怕你个拎棒槌的。”
从此邱寡妇的泼性便收敛了许多,逢人也没那般刻薄了。有时走道碰巧遇上二爷,多是眼皮不敢抬,大气也不敢出,顺溜着墙根子过去。
二爷也有极其可爱的一面,这种可爱劲随着他岁数的增长,表现得越发显露。我上初中时,二爷又老了一些。一个秋末的傍晚,我进二爷的灶屋给二爷烧锅,二爷拿出一把姑姑送来的香蕉,剥了皮放瓷碗里上锅蒸,说这样加热后,吃了肚子就不会疼。一番忙碌后,二爷掀了锅盖去找香蕉,只剩下空空如也的碗。
二爷那天吃了中午饭,独自蹲在院墙外,徒手拔地上的枯草。我和二婶子上前,劝他回屋里休息。二爷说着话,说着说着嘴角就不止地流白沫。二爷不住的用手去抹,抹着抹着嘴便不听使唤了。我和二婶子赶紧叫救护车。一路颠簸到了县医院。二爷逐渐陷入了昏迷,医生诊断后,说是心肌梗塞。
二爷昏迷了两天,期间醒来,就仓促地喊我,我把耳朵靠在二爷的嘴边,二爷重重的喘着气,说道:“回去吧,文艺,听我的话,咱回家去,我累得不行。”
众人极力劝阻,二爷不听,凭着最后的一丝力量,拔掉了鼻孔里的管子,抓掉了前胸,腿部绑带的仪器……
二爷活着卑微,去时坦然,随手一拔那根氧气管,拔掉了与这个世界相连的脉跳。二爷从容的朝我们挥了挥手,便咽了气。
二爷走时,七八个汉子抬着二爷。二爷稳稳的躺着,脚蹬着麦田,沉沉地睡了。
从此我踏破铁鞋,在这个阳世上,再也找寻不到二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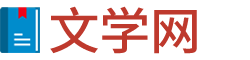 返回首页
返回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