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孵
北风在湖乡旷野上空,向右转了一个身。稻田里刚播撒的乳白色硬谷芽,噌噌冒出了碧尖儿,盎绿着往周遭不断扩散柔软朗润。沟渠沿边丝滑的水藻苔藓丛带,黏附了团团墨绿色的珍珠粒蛙儿蛋,它们比湖鸭更先知:春水究竟暖几度?东风吹起水波皱眉,眼急着催赶那些黑色的、灰色的小蝌蚪儿,晃头摆尾使劲游弋,倏忽间,抻出了四条腿,欢快蹦跳上岸。跟着春耕脚步一起上岸的,是一场萌发蓬勃的家禽春孵。
湖乡渔村无山无冢,一望无际的平阔辽远。错落有致的屋舍,在水的另一方,平添几分宁谧安详。农家报晓的“闹钟”雄鸡,打破之前安静沉寂的黎明,调早了响铃,天亮得早了,人们醒得早了,也起得早了,春光在缩短的睡梦中,拉长了勤快的身影。
此时,一只怀揣春天的老母鸡,犯起了“春困”。它不再像往先那样,整日高唱着颂歌“个个大”,而是懒散地蓬松着羽毛,一副昏昏欲睡无精打采的模样,还不肯将就着随地而憩。它似乎在寻觅一个安全隐蔽的角落,慢腾腾地围着屋子转悠半天,终于瞅准了屋后那堆倚着大桃树码起的旧稻草垛,它在草垛底下筑巢栖身,“咕咕咕”地低调哼吟着估计只有桃花苞蕾能听懂的“摇篮曲”。
一只橘色家猫睁着线眼,慵懒地蜷躺于瓦背,胸腹下贴着几只乖巧的杂色毛幼崽,母慈子“笑”般共享午间和煦春阳。隔着一扇篱笆墙的邻家大公鸡,扑翅跃过来,与橘猫对视稍许,许是觉得无趣,忽然从瓦背上飞扑下去,落脚草垛边,啄住蹲伏的老母鸡头顶浅冠,骑到老母鸡背上欺压它。我顿觉心有愤愤不平,举起长竹棍慌乱扑打邻家公鸡,结果扑断一枝开得繁盛的桃花。外婆的老花远视眼,瞧见了这一幕,竟不怪邻家公鸡过分逾矩,也不怪我打夭了好多桃果。她欣喜地跑过来:“咱家母鸡赖‘抱’了,春‘抱’可是最好的时节啊!”外婆赶急赶忙将老母鸡捧回屋内,找来箩筐和篾罩,为它打造了一个圆满舒适且加罩盖的“月子”窝。一日三餐精米细粮侍奉窝前,“赖抱鸡”温顺不贪玩,开盖吃食排泄后,只在窝边闲散几步,便自觉进窝专注干它的孵事。
我不知道渔村人为何要把“孵”说成“抱”?也许他们认为仄声高亢的字眼,更能凸显出旺盛的生命力吧!
他们一说到谁家有“赖抱鸡婆”,村中妇孺便争相奔走,积极为主家筹蛋换蛋。渔村人胸怀像大湖一样宽广,还有“借抱”“搭伙抱”的。老母鸡的胸怀也很宽厚,抱一次能容纳二三十枚蛋,哪怕不是自己亲生的鸭蛋鹅蛋,也会毫不偏心地均匀翻转,付诸等量温暖。
老母鸡孵蛋到一定的时日,外婆在鸡窝前来回踱步,喃喃自语:“鸡呀鸡,二十一;鸭啊鸭,二十八;鹅啊鹅,一个。”小鸡需孵二十一天才出壳,孵了几天之后,为了不消怠老母鸡的热情,要进行“胎检”筛选。没有漏洞破绽的孵蛋,外壳越发轻薄光滑,不好拿捏。有几个夜晚,我举着煤油灯帮外婆照孵蛋,外婆小心翼翼,反复向我确认:“看见蛋中阴影黑斑没?”我点头,她就把蛋放回窝内;我若摇头,次日便有吃掉几枚煨寡蛋的“任务”。
那寡蛋味,不及鲜蛋,远远散发出一股腥臭,蛋白蛋黄混夹一起,实在难以下咽。可我怕听到节俭的外婆那一声叹息:“浪费可惜了。”也怕听到慈悲的外婆那一句嗔责:“再莫打邻家公鸡了。”外婆最后连哄带骗,说寡蛋虽不香,但吃了补身体。这话征服了我的不情不愿。
小鸡出壳前几天,外婆还要来一次孵蛋“点水”。孵蛋放入温水盆里,沉入盆底的,彻底淘汰出窝;浮在水面摇动的,又放回抱鸡窝。老母鸡不厌其烦地用长喙啄破蛋壳,小鸡探出头来,它们自己还会伸腰踢腿,缓缓挣脱蛋膜的束缚,扑棱着湿漉漉的小翅膀,钻出来,趔趔趄趄试步……很快,抱鸡窝里传出一阵“叽叽叽”的叫声,像是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宣告一个新的生命诞生。
不,不止一个新生命。一场春孵,命运之神悄悄收走了所有的遗蜕,啄破冬夜暗黑的藩篱,送你一个温暖光明的新春天。你看那春草茵茵的堤坡上、碧青的湖泊沟渠面、灰黄的屋舍檐墙下,茸茸毛色起,春雏已成群,一派欣欣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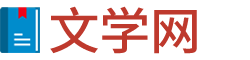 返回首页
返回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