袅袅炊烟
村头有一片四四方方的田地,每家每户的地都被田垄隔开,打眼望去整整齐齐,一丝不苟。这片田属于村集体的自留地,平日里乡亲们盖房修圈,都要在这片地里取土,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土壕。
在我的记忆中,洋槐树最高的那根枝丫的头都没能伸到壕上面去。每当拉着载满庄稼的架子车从路上俯视壕底,父母总要叮嘱,别在边边上去,小心掉下去!
但是在我的眼里,这座壕就是最有吸引力的游乐场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那里的农村小学执行的是半天课时,早上去的早,下午不到三点就放学了。周五放假还会更早一些,往往是日头还高挂天上,我们就麻利地把书包放下,三五成群吆喝着向土壕出发了。关中平原上气候干燥,土壕里尘土飞扬,清脆的童声在壕壁上来回反射,久久回荡。
虽然好玩,虽然贪玩,但按时回家吃饭的自觉性还是有的,否则免不了一顿饱打。虽然没有手表,也没有手机,但我们有着精确的时间参照,那就是看村庄里的烟囱有没有冒烟!
在那个年代,关中平原上的农村大多都是厦子房,一道公墙两家用,相邻两家各自依托公墙搭建斜顶青瓦屋面,省了成本还便于维系邻里关系。厦子房后面是一个独立的厨房,每个厨房屋顶都耸立着一根烟囱。每到饭时,当土砌的灶膛里秸秆燃起,一柱柱青烟就在屋顶飘荡,在半空中变幻着各种样态,向我们伸出召唤回家的手势。
第一柱青烟通过光线传播到达眼里,只是结束打闹嬉戏的前奏。有胆大且皮厚的伙伴,很多次都是语出惊人:"那是我妈在烧羊圈的草呢,不是做饭哩!"
至少是很多柱炊烟都冉冉升起,汇集在了村庄上空,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硕大而明显的手势之后,我们才摸一摸昨天刚被鞋底子揍过的屁股,不甘心地拍拍身上的灰尘,相互打量一番,方捡拾起各自的"战利品",比如被幻想成坐骑的树杈子、挎在腰间的木头枪、红苕杆制作的"项圈"、从壕壁隐秘处挖到的"崖娃娃",诸如此类等等,携带着下一次的念想,朝着炊烟升起的方向走去。
由于搭灶技术的差异,灶膛排烟效果有所不同。有时候遇上吹倒风,一股白烟就会从灶膛倒灌出来,正在做饭的母亲被呛得咳嗽连连,赶忙指挥我把灶膛里的柴火拨开,再使劲拉几把风箱。风箱叶扇就紧张地拍打着风门,"吧嗒吧嗒"的声音充满了生活的节奏感,在庭院里荡来荡去。
下雪之后气温骤降,母亲把早饭都做好了我还赖在炕上不想起来,找借口说棉袄太冷。母亲就把棉袄棉裤拿到厨房,就着灶火烘烤片刻,揉成一团把热气捂着,迅速地冲到跟前。炊烟格外喜欢棉花和粗布,毫无保留地把烟火味渗进棉花里,那种味道闻起来也似乎带着迷人的气息,给人以无穷的力量。
村里有一口老井,全村人生活用水都要靠它。我不知道水井的年龄有多大,只记得水井口的青石已经被绳索勒出了深深的沟痕。钩桶相碰、挑起扁担的第一个声响,既清澈又干脆,既紧张又急促。当沉睡中的村庄被突然唤醒,天才麻麻亮,父辈和他们的父辈们早已知道,灶膛里的火已经燃起,随即而来的就是穿透清晨直达心肺的炊烟,它在提醒着每一个休憩了整晚的生命,新的一天又来了,该起来劳作了!
辘轳把绳子一圈一圈缠在身上,吊起满满一桶井水之后又开始下一桶。鸡鸣和犬吠此起彼伏,桶里的水跳跃而出落进土里,潮湿而凝重的气息浸入炊烟笼罩的村庄,与挑水者厚重的脚步完美融合,在一个个周而复始的清晨,形成了富有生命张力的场景。村庄之外,大地早已散发勃勃生机,几只麻雀从树丫附身飞落地上,扬起脑袋机警的观察着四周,旋即又飞向另一处田野,翅膀扇动着雾气,划破了一整张天空……
渭北旱塬人的早饭极其简单。春夏秋三季就是馒头和锅盔馍,冬天熬上一锅红苕包谷糁,包谷糁必须要用废秸秆,以软火慢慢熬,灶房里就一直充盈着青烟的气息。用萝卜腌制而成的咸菜是早饭时必备的主菜,切成细丝状之后装进盘子,在菜丝面上搁一点辣椒面,铁勺里倒点油伸进灶膛烧煎,带着柴火的烟气泼在菜上,"滋啦"一声,满屋里都是浓浓的油香和蒸汽。待烟雾散去,大半个馒头已经下肚。填饱了肚子,该干活的去地里干活,该喂养牲畜的在圈里忙着。这一赶早就忙活起来的锅灶和炊烟,就像是不可抗拒的号令,指挥着人们奔走在厚实的黄土地上,忙忙碌碌,不敢懈怠。
后来我和许多小伙伴一样,去了离家十几公里远的地方上高中。每周五放假,我们骑着吱吱作响的自行车,一刻也舍不得耽误似的往回赶。放学时候恰逢家家户户开始做下午饭,时不时有炊烟携带着饭菜的味道,不紧不慢地穿过村庄旁的公路,这似乎给了我更多的力量。颠簸的路途抵挡不住回家的激动,我的双腿摆得更快,双脚踏得更欢,自行车轮似乎要从路上飞驰起来,耳边灌满呼呼的风声……到了,到了,当自己亲爱的村庄出现在眼前,一缕缕炊烟正在屋顶和树冠之上,随风缓缓舞动,熟悉的味道指引着车轮前进的方向,就好像闭着眼也能驶向自己的家。
每一柱炊烟传来的味道,都是不一样的。就像母亲端来的一碗手擀面,虽然原料无异、调料相同,但就是有着吸引儿女的独特口味,令每一个归来的孩子都胃口大开,齿间留香。
每一柱炊烟升起的样子,又都各有不同。东家的炊烟泛白,西家的炊烟带青,前院的炊烟稀疏,后院的炊烟浓烈。我站在村口的门楼旁边,一眼就能分辨出哪一柱炊烟是来自自家的烟囱;从炊烟升起的样子,就能猜得出母亲做的什么饭。或许,这就是生命的本能,让我永不迷失。
离开故乡二十多年。同样是在厨房做饭,身上只是油烟,再也没有烟火气息,也闻不到棉衣里的柴火味道。逢年过节,打着回家陪陪老人的心思,有时候却不禁感到是在走程序,寻求心理安慰。村子里的土房子都拆完了,拔地而起的都是砖混结构的楼房,不想在老宅子修房子的也都搬到县城去了。我沿着村庄内的干净而又整齐的水泥路闲转,两边的房子都修的高大宽敞、气势宏伟,但大门敞开的人户不多。走到村东头一个小时候玩伴家门口,地上的落叶已经厚厚一层,朱红大门两侧的对联在风吹雨淋中已经残缺不齐,但还坚强地守在墙上,似乎在执着地等待着主人归来。
按照惯例,每次回去要到家族里已逝长者的坟头烧点火纸、整修坟包,以寄托哀思。我默念着归乡太少的愧疚,心里却像塞了一团棉花,堵得发慌。回到家里拿出手机拨弄着,母亲似乎是在给我说话,又好像是自个自的唠叨,村里对烧秸秆管得很严,现在提倡使用节能灶,做饭很少烧秸秆,土炕也挖了,冬天早晚也没有烟熏缭绕了。我问她眼睛怎么样了,母亲说白内障症状似乎没有再加重,每晚上坚持滴几滴眼药就行了,这让我心里很是慰藉。母亲曾说过,那些年日子紧张,灶火里烧不起煤,只能烧麦秸和包谷秆,熏坏了她的眼睛。她还说起了我小时候给屋里烧炕,结果给炕里塞的包谷秆太多,烫得我半夜醒来直往炕边边挤。
听着听着,我似乎又看到了那个如今早已不复存在的土壕,我正站在土壕上边,看着村庄上空刚刚升起的袅袅炊烟,分辨着哪一柱是出自自家烟囱,不由自主地朝着炊烟升起的方向走去。我低头走着,费力地走着,走到一半的时候抬头一看,竟不知走到了哪里,方才的炊烟早已消逝不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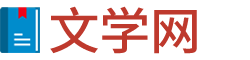 返回首页
返回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