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爷的哲言
因为沉默寡言和善思多虑,使他几乎成为独行者。曾有的两个老婆,难以与他搭言而都郁郁寡欢。据说,前房是个好静之人,本来言语不多,只用眼神、手势与他交流,就连这,也很少得到他的回应,气急了就说:死木匠,真是个木头!二房极其活跃,逢年过节或遇红白喜事,总爱唱几段花鼓、扭几圈秧歌,对他也是热茶热饭、热言热语的,而他的回应则只有点头、摇头两种。儿女八个,个个精明能干,却没有哪个与他谈得拢,时常的交流是"你去弄啥弄啥",或"啥事你没弄好".然而,怪就怪在个个极其遵从他,孝顺他。
第一次与他同桌吃饭,是我上小学五年级时的正月初二,或许因为过年,或许因为他心情很好。按说,我们相距十来里路,交往很是频繁,但在过去的历史中,从未享受过这种待遇。在我的记忆中,他一直是单独吃饭。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物质缺乏,他是家中的顶梁柱子,由于人口太多,外婆一直让他单吃:午饭只一盘菜,晚饭加一壶酒,无论冬夏都在火炉房的那方木桌上。他家年节也不一般,除了外爷、外婆陪客外,别人一般不上桌子,我们这等辈分中的成年人也根本不行。尽管舅舅当时已是大队会计,如他不喊,亦不得入座陪客。
这年正月初二的午饭,没有别的成年客人,外爷在熊熊燃烧的火炉边取暖,桌上有四荤四素八道正菜和一壶烧酒。刚一上齐,围炉而坐的舅、姨和我们这帮前来拜年的孩子们自觉到灶房吃饭,他却用烟袋杆子指着我说:就在这儿吃。我用目光望着慈祥的外婆,外婆拍着我的头笑道:你就在这吃,也好帮你外爷倒酒。
那年他有多大岁数,我弄不清。在我的记忆中,从第一眼相见,到三十年后他离别人间,似乎就是这么个形象:腰是弯的,像个问号;头发稀少,几近秃顶;脸色,头皮全为蜡黄;一双手永远也伸不直十指,但他的肉量、酒量、饭量却是常人无可比拟的。
他先把一只二两酒杯倒满,问我喝不,我说不喝,他嘿嘿一笑,一口喝了,长长地、陶醉地哈了一口酒气,就伸出筷子夹肉,一口气把筷子厚、半尺长的蒸肉片子吃了四片,才气呼呼地用筷子敲着桌子训我:咋不吃,连肉都不知道吃,啥用!于是,我和他一人一片,相跟着吃完一碗粉蒸肉、一碗豆酱肉片、一碗酸辣子炒肉片。他再灌两杯酒,吃了几口素菜,就揭开蒸肘子上的盖碗,连吃两块,问我咋不吃,我说吃不动了,他问吃饱没有,我说吃腻了,他嘿嘿一笑,说声往饱吃,就端在手上,连肉块带油汤一扫而光。完了,打两个饱隔,喝两杯热酒,又长长地哈两口热气,对我说:去端饭。我一到灶房门口,外婆就知道干啥,让我不管,她自己用托盘端了三碗米饭过来,也坐下,边给我夹菜,边陪我们。外爷先用筷子刷刷刷地向嘴里刨了半碗米饭,然后把半碗菜朝饭碗一扣,一口气吃完,连四姨适时送来的一碗蒸饭汤,也喝了,就拿过煨在火炉边的茶缸,灌一口水,呼噜噜地漱了口,自顾抽烟去了。这顿饭,按我的统计,抛去别的东西,他所食用的饭、肉、酒均超一斤,真是海量!
我刚放下饭碗,他就从墙上的搭杆上取下一把镢头扛在肩上,说:跟我上坡。外婆劝:过年嘛,你……他没理,拍着我的头说:吃饱了,好做活。别人见我跟他去了,都没反应。在这个家庭,不管男女老少,均听他的安排,他没吩咐,你别乱动。
到了后坡的地里,他挖地,我捡石头。可能因了肉和酒的热量,加上用力很大,在风雪呼啸的寒冬中他竟热得上身只剩单衣还满头大汗,而我却冻得青鼻长流,并被那冻冷的石头把手指折磨成了冰棍。他嘿嘿一笑,歇伙抽烟,让我去挖,两袋旱烟工夫,我也出汗了。他就说:饿死的懒人冻死的狗,养力的大肉壮胆的酒!我似乎明白了什么,赶紧问:都说你胆大, 白天敢打狼,晚上敢打鬼,是真的?他说酒壮英雄胆!我又问:都说你杀气重,不理人也不吵人,可是都怕你,为啥?他说:只要你吃饱了,啥人都能装到肚子里去,还有啥说的!我问:都说你这腰是出力过多、过猛,挣断的?他说:郎中混个夜夜跑,木匠混个弓弓腰。
外爷是个木匠,方圆百里有名。我家两个姐姐的陪嫁桌柜都是他做的。出嫁大姐时,家境贫寒,且不准大办婚事,陪嫁只有一只箱子。到了出嫁二姐时,条件好了,可以做大衣柜、五屉桌和大箱子了,大姐看了流泪,不好说我父母,只说外爷偏心。外爷生气了,丢下斧子,跑到房后的一丛林子里,把头抵在树上,大口大口喘着牛一样的粗气。我跟去,不敢劝,只是抓着衣服扶他。外爷把头在树上碰了两下,转过头来,长叹一口气,反又劝我:你别哭,我是在想事呢。我问:你思考问题的方式,就是碰树吗?他嘿嘿一笑:有时还碰墙呢!想不通时,头都急得胀疼,不顶几下,碰几下,咋得行?不像你们念书的呀,我没文化,想不展妥事情,只能硬碰硬。光碰人不好,有时只好碰东西。我听痴了,望着外爷的满脸皱纹,泪流满面,并在心中发誓:要好好读书!
从林中回来,看我母亲伤心落泪,外爷就劝我大姐,不让她再闹了。大姐不听,赌气说:我不管,就要闹!外爷一头站起来,扔了斧子,凶声凶气地说:你惹的事,你不管,谁管!你是大人了,给我记住:谁都不能靠别人,真正管你的,只能是你自己!一句话,喝痴了大姐,并让我明白了一个大理:真正对你负责的,永远是你自己!
外爷这个文盲,用他饱经沧桑的阅历,一语点破了如何做人、如何处事、如何自立的人间真谛。
这天下午,我没看书,也没做作业,一心一意地帮外爷干木活,一会帮他牵线,一会帮他拉锯。当那奇形怪状的原木经他打磨,变成了光滑的条子、板子,有了直角、锐角和正方形、三角形之后,我真切感到:外爷不光是个木匠,简直是个艺术家!
但这个艺术家,却有半辈子是偷着做木工的。自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公社化、食堂化"开始,直到八十年代初期,都在"集体化"和"反对大操大办"的环境中遭到限制,那木活是不能大方去做的,否则就会收了工具或木器。或许正因为如此,外爷练就了月光下干活的本领,并能在一两分钟内把一口箱子拆成木板,到你查问时,他只说:盘弄几块板子嘛,没做啥!
他把一个农民的智慧与时局需要敏锐巧妙地结合为处世之道,所以,无论在"四清""路线教育"等"斗私批修"的任何时潮中,既不吃亏,也没得势,总是那样以他的活法滋润地生活着,让十口之家的日子总是比村上的别家过得有滋味儿。何况,七个女子分别组建七个家庭,还需时常接济一些。这些开支,全赖他的手艺。别人付酬时,不管给粮给钱,他从不张口要多要少,都是人们凭心而定。给了,他总要多少退一点;一时给不起的,他从不去催。所以,人们总觉得欠着他的情,也就时时念着他的好。尽管,有人私下请他做过活儿,后来以"私心太重"揭露他、批评他,他也不言传。那人没趣了,只好恨自己:给不起钱就说句好话嘛,整人家干啥?自己瞎眼睛了!
因此,外爷晚年生病后,四邻八乡的人都奔去看他,那礼品足能养他再活一辈子!为此,我曾向他打趣:知足了吧?他十分艰难地使着力,发出低沉而坚定的声音:活着只睡一张木床,死了只睡一口棺材……人心莫贪多,多了就是祸!
这个木匠!临终依然论木,遗言仍是哲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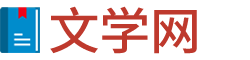 返回首页
返回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