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片灯火
回村的路上,偶见几处枯树上飘摇的粗衣,像是谁在招手。无人问津的果子,自由飘落。遍地疯长的野草,漫过爷爷的坟茔。篱笆墙的影子呢?黄发垂髫呢?众狗狺狺呢?整个村庄似乎只剩下几栋关门插锁的楼房。钢筋水泥在日夜歌唱着时代的变迁。一条被野草磅礴亲吻的蜿蜒公路,因车辙稀少而身体硬朗,神清气爽。
这是我深情缱绻的故乡吗?是我梦里眺望的星辰大海吗?
一路忐忑,走进幼时依偎的院落。那个昔日住着十户人家和几户燕子的杨家大院,如今只剩隔房堂哥老两口。两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扶着岁月寂寞的栏杆,守着新建的楼房,与阒寂无人的家园耳鬓厮磨。年轻的主人们则对他乡想入非非,散落天涯。老的些则病的病,死的死。跑得动的都住进城里帮忙带孙娃子,也难得回来一趟。年轻人有的过年还能匆匆回去几天,有的房子修好几年也没回过一次。没修房子的有些人,听说早年去南国捕鱼,到北疆种棉花。又入矿山、工地,一路飘摇,直至带着故乡的胎记下落不明。
我家的老屋早年就卖给了堂哥。堂哥那时是个有名的石匠,錾子铁锤玩得溜转。他家养了五个儿子,读书少,劳力壮,却没一个愿意做石匠,都凭一身劳力远走高飞。在梦里不知身是客的他乡,把卑微的灵魂抵押给苟活的城市,把迟暮的父母托付给贫瘠的山村,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一个叫作“打工”的词,多年来鲜有回家。好端端买来的房屋闲置不用,眼看风吹雨打,荒草蓬勃,摇摇欲坠。堂哥见儿子们依然无人肯回,气得在一桌无人问津的团年饭面前乱骂,狗东西,滚!
后来,院里开始新建楼房,堂哥一气之下把心事交代给了冷眼旁观的挖掘机。眼睁睁看着土墙瓦片一坨一坨地倒下去。尘土飞扬间,他仿佛看到自己曾在深山老林的打石场里,一锤子一錾子满手血泡累死累活的样子。便一勾子瘫坐在地上,捶胸顿足,怄得上气不接下气,众人拖都拖不走。本想用自己的血汗,换来儿子的成家立业,人畜兴旺。结果,鸡飞蛋打,人去楼空。后来,堂哥偶尔接个广东打来的电话,偶尔收到一张新疆飞来的汇票,他也面不改色地骂。
最后,买来的老屋成了一块被抛弃的平地,水泥硬化后变得光生平整,却只好用来堆放各种杂物。在那光生平地的身体里,似乎长着一双清亮的眼睛,偷偷见证着堂哥老两口,他们一生潦草的生命,终将寂寞地走向终结。
我也是故乡的孩子,曾在天涯遥望,眼里的星辰大海便是回家的征途。如今终于站在这块土地上,感慨万千。没有聒噪的声响,院子静得让人窒息。曾经的活色生香、飞短流长,都成了褪色的历史。阔别的游子啊,在故乡一往情深的期许里,试问,云中谁寄锦书来?
这个焕然一新的杨家大院,这个曾风吹散稻花,撒一路金黄的故园,如今,却到处都生着无人问津的病灶。
哥嫂陪我走出大院,沿着乡间公路行行重行行。放眼望去,我已唤不出一个熟悉的地名来。一是离别家乡岁月多,二则因修房筑路,再就是荒芜的大片土地,被疯长的树木野草几乎连成一片,分不清原野里曾经的张三李四。两位向导一会儿说那是柿子梁,那是老树湾。一会儿又说这是陡陡坡、沙松岩、老岩堑、大松碥……
前面就是李家大院,平时也只住着两个老年人,那老太婆可能也快……堂哥平时只顾抽烟不甚言谈,今儿却喋喋不休。他边说边卷了一锅叶子烟,点燃并深吸一口后,喷出浓烈呛人的烟雾来。我隐约看见,他那张被烟雾弥漫沟壑纵横的脸上,似乎因一个归来的听众正泛起一簇簇彩云。他站在路边,把颤巍巍的身体拼命往前倾,想穿破山野的氤氲,看看那两个稀薄的生命尚能饭否。走着走着,路边几座新坟突兀,我定睛一看,其中一座墓碑上赫然刻着一个熟悉的名字。老嫂子指着地下的人说,个背时砍脑壳的哟,才造孽啊!一个人在屋头,搭了急病莫人晓得,滚在柴屹崂里死得梆硬……
走进李家大院,院里也是焕然一新,旧时的瓦房早已不知去向,几栋新楼却沉默不语。几只公鸡和两条土狗,围着一个须发皆白的耄耋老人尽情撒欢儿。老人正在大声武气地打电话,电话那头是他的老伴,已住院多日。只听老人对着手机说,喂,老婆子,今天顺门样了?想吃啥子就吃,莫是舍求不得,又把方子(钱)弄来藏起嘛,你那老毛病……
其实他早就知道老伴儿耳已失聪,听不见他的挂牵。他仍然照例说,天天说,细声说,大声说。除了说给老伴,说给儿女。更像是说给房子,说给土狗,说给水田,说给花草……
见我们去了,老人放下电话,拉着老哥嫂闲言碎语,时而长吁短叹,时而又笑得咧开了嘴,但他已然不认识我了。尽管少时的我和玩伴们,曾大摇大摆地溜去他家那片蓬勃的高粱地,把眼睛鼓成铜壳子大,去揪那些因体内藏着秘密而被主人忧虑的诱惑。那些生来就被食客们惦记的家伙,通常活不过它的盛年。那天,我们几个细娃儿食客手忙脚乱地掰断了一大片。慌乱中,没有孕育蜜汁的饭高粱也被误伤倒地,然后拖起宝贝就跑,结果蜜汁还没下到肚家坝,就被撵来的家长破口大骂,背时起瘟的些,给别个整成这般尸形,咋跟懒肠子二哥交待哟?背万年时的些,饭没通够?还是胀饱了不消化……家长们边骂边操起棍子撵得食客们个个奋不顾身地到处乱窜。是啊,那些浸染岁月的人间烟火,一如旧年房顶上的炊烟,早已随风飘散。
如今,三十年来,半生漂泊,心无论漂到哪里都无处靠岸。重返故土,已是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本想归来再看你一眼往日的容颜,匍匐在你温暖的胸膛,为你浅吟别后的沧海桑田,你却瘦成一纸凌乱的背影。时过境迁,就算耗尽笔墨也换不来旧时那动人的诗篇。
晚上,我陪着老哥嫂坐在昏暗的月光下,听他们抢着讲述村子的经经绊绊,以及他家五个劳动力有限的活动范围。他们无力篡改现实,只能用苍凉的声音对峙孤独与无奈,对峙希望与绝望。待月光撒下一张银网,收走虫鸣鸟叫后,他们便彼此扶携相依而眠。
我独自一人,徘徊在往事门前,归来的兴奋被生了病的风吹起一丝疼痛。
曾经,我家就在洼的岸上住。
那时,草草杯盘,昏昏灯火。农家院落里,也不乏纯朴天然的乐事。农闲或下雨天,大人们最爱坐在一起打纸牌开玩笑,每次笑得推来搡去眼泪纷纷。晚上和娃娃们一起守着我家那台村里最早的黑白电视机看得状况不断笑骂不停。那个大字不识的方言解说员大妈,在人人都能懂的剧情里,她非要强制解说。闲不住的嘴巴,把好人夸上了天,把坏人咒入了地,祖宗十八代都翻不了身。看《霍元甲》时,几个舞着枯草火把来的农妇,看到霍元甲为民除害,扯破嗓子吼加油。发现耍流氓的龙海生,就像跟他祖上有仇似的,气得妇人们个个咬牙切齿的脱下满身泥污的胶底板鞋,扬言要扇他几耳光。嘴里都在骂,个背万年时的,起瘟的,砍脑壳的……一场电视看完,简直是吵吵闹闹惊心动魄,惹得满院月光也忍不住咯咯咯地笑出了声。娃娃们最大的快乐莫过于玩捉迷藏。在丰年蛙声的伴奏下,在人影幢幢的月光里,藏来躲去不亦乐乎。可如今,灯灭了,蛙声也枯萎了。曲终人散的乡村,被辽阔的空空荡荡冷冷清清重重围困,惟有满脑子鲜活的记忆沸腾不止。我仿佛闻到旧年的稻花飘香;仿佛听到少时玩伴们龇牙咧嘴的呼喊;仿佛看到父辈们操持农活的辛劳;以及为了一颗糖,卖糖人竟一个个坠入父母嘴里鲜活的谣言深处……
月光时而躲进云里,山里的夜晚更是陷入无边的黑暗。我怕这不知情的黑,蔓延至老人孤独的梦境。于是,踮起脚尖张望夜色之外的万水千山,兜里一直守口如瓶的手机,此时却不安分了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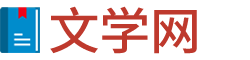 返回首页
返回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