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里乡里
我有两个家,城里的家和乡村的家。城乡之间相距不远,驱车一个小时可以到达。乡村的家是我的祖居地,历史久远;城里的家,也就十几个年头。
无论去哪个家,归属感都无需过渡。打开门,撞入眼帘的就是熟悉的环境,那些桌子、凳子、锅灶,房间朝向,甚至毛巾悬挂的位置……所有这些,即便闭上眼睛,都能毫不费劲地摸到。
但睡一觉醒来,却往往把城里当做乡村,把乡村当做城市;迷迷瞪瞪,怔怔地看窗外,识别半天,思想半天,这才确定下来。出现这种错觉,是因为睡梦,因为潜意识。乡村和城市,都在心里刻下极深的印记。
房子,是安放身体的场所,也是心灵的栖息地。有了一处挡风避雨的地方,人的心才会踏实,才会有念想。
每次,自老家的住所去城市,或者自城市的住所去老家,都习惯说"返回".回头是一个家,再回头,还是家。
上午,老家的菜园覆一层阳光,一两滴露水挂在叶尖;拣那些长得成型的、较嫩的菜薹,采上几方便袋。还有青蒜。这些,是我去年深秋种下的,不施化肥,不喷农药,全天然。一个小时后,回到城里的家,打开袋子,菜薹依然水嫩。
城市和乡村有太多的不同之处,有表有里。夜晚的城市,是白昼的延续,人们在夜色里越发精神,马路上人来人往;乡村呢,一团漆黑,但抬头却有星光。城市的夜晚延续白天的喧闹,乡村的夜晚宁静清澈。
城市的公园,四季都有鲜花缤纷。春天,红梅、迎春花领唱,樱花、百合、杜鹃花……次第亮相;夏天有榴花的火红,有紫薇串连春夏;秋天,木槿花最为靓眼,一大朵,似乡村的棉花,粉白相艳。冬天,公园沉寂了,树木都进入了沉睡。腊梅,不经意间放出一片明黄。
乡村只能呈现平实,呈现劳作,乡村只有厚重的土地,只有四季庄稼。小麦,油菜,稻浪,间或有几块棉花地。乡村给繁华世界预备着所有的食粮,乡村是世界的厨房。
夏天的傍晚,田野里蒸腾起一缕缕水气。泥土的味道,充盈在水气中,鼓涌而来。那味儿并不好闻,但醇厚,深吸一口就醉了,那是一整天阳光酿就的美酒。扛着锄头,踏着夕阳回家的乡亲们互相打趣,一天的疲累,就在随口而出的谈笑中烟消云散。
城市的公园里人流穿梭,几乎没有认识的人。擦身而过时,你我互瞧一眼。为着气质和素养,都绷着同一副面孔,莫测高深、器宇轩昂。连路边的树木,都肃然而立。
或者说,来城市是冲着个性的独立,冲着喧闹中独特的个体、繁华中特有的宁静。回乡村呢?是奔着个性的释放。土地是无垠的、阔大的,它容纳张扬,也容纳内敛。土地里沁出的味道、树林里滤过的风、庄稼勃勃生长的劲头,都是我们回来的理由。我们需要漂洗,需要换一个脑子。
不断更新的时代,造就了特别的城乡互动。昨天的面貌是农民,而今天的傍晚,换上一身运动服装,我就是城市的一分子,跟你擦身而过时,我带起的风声中有乡村的味道,不知你嗅到了没有?
老舅家跟我隔着一户人家,多年的邻居。叫他老舅,因为他的外甥就住同一个村,大家就仿着他外甥的口吻。老两口前些年去了城里的儿子家,一住十几年。前年回来了,老舅妈变化不太大,但老舅却挺一个大肚子,长胖了,走路吭哧吭哧的。他自己笑话自己:活像九个月的孕妇。
我问他,是不是长了个东西?去医院瞧瞧啊。他摇头:不是、不是,就是闲的,没毛病。
回到老家,老舅和老舅妈整修房子,开垦荒地,路边地头的闲地,能种的都种上庄稼,忙碌不停。今年一见面,老舅恢复了原样,大肚子没了,有说有笑。
我居住的城市小区有七十多栋楼,农村来的人居多。那些带孙子的爷爷奶奶们,跟老舅老舅妈神似,衣着和神态都是乡村的做派,在超市里购物也高声大嗓。不相识的邻居间,几句话就能唠成知己。你说,是城市改变了他们,还是他们改变了城市?在这里,没有了城乡之分,有的是各地乡音的汇总,各地风俗的集中展示。
就像我自己,住在城市跟住在乡下,几无差别。有人让我出示简历,我坦然地说:我是农民。
夜晚,我走进喧嚣的城市。璀璨的霓虹,车流如水一般奔腾的马路,都是城市独有的面孔。路灯亮了,灯光剪岀我的影子,后一个路灯让我的影子前行,前一个路灯又让它退后。前面,是一组灯光耀眼的高楼;后面立一块铭牌,镌刻的文字表明,这里曾是一座村庄:柳树郢。
前后路灯殷勤投射,一次次把我的影子推向城市,又一次次拖回村庄。我就这么迈步,一脚城里,一脚乡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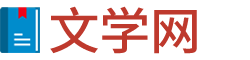 返回首页
返回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