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原上的母亲
从潜意识的梦中突然惊醒,发现自己身处白茫茫的冰雪高原中。前所未有的孤独感袭扰着全身,无助地高声呼喊着母亲,总觉得母亲就在前面,可无论如何也抓不住母亲的衣袂。我就那样光着脚,在冰原上奔跑着,奔跑着……
打记事起,我就开始不断做着这个梦,醒来后总是第一时间蹑手蹑脚走到母亲的床前,每当看到母亲安然入睡的样子时,又总是满心欢喜,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母亲在娘家姊妹中排行老三,老家的人都称呼她“三姐”“三妹”“三姑”“三姑婆”,似乎从没听谁喊过她的名号。她是国字辈,在老家李姓中辈份很高,不管是哪家多大的岁数,都要恭恭敬敬地喊她一声。乡邻对母亲的尊崇,不仅仅是因为她辈份高,更多的是她执守一辈子的善念。母亲一生未曾念过一句书,但她恪守中华民族的诸多传统美德,胜过许多的读书人。她正直无私,遇事忍让,不与人争长短,不背后论人是非。“人前不舔肥,人后不说短”,这是母亲常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记得小时有一次,三哥犯了一个我认为不大不小的错,我忙不迭的在母亲面前告了三哥一状。原本想会得到奖励,不曾想,母亲当即就给了我一巴掌。她教训我道,哥哥犯了错,你应该想办法去帮他补救,而不是跑来告状,讨好卖乖。这件小事情让我铭记终生,母亲的教诲也深刻影响着我职场生涯的个人修养。几十年后的某一天,我的上司同我发生龃龌。他的一次不是很规范的额度较大的差旅费报销,在例行的审计中被作为问题线索上报给纪检部门。这位老兄疑心较重,怀疑我利用这件事做文章,便托同僚给我带话。参加工作二十多年,我第一次与自己的上司争吵,也是唯一的一次拍桌子。我指着那位仁兄吼道,我某某人毛病很多,但我家的家教和传统读书人的性格,不允许我在人后说三道四。母亲的这种品质也影响着每一个家庭成员。我们家是四代同堂近四十口人,无论老少,包括嫁进我们家的媳妇,在老家都有好的口碑。后代当不当官,挣不挣钱,母亲对此没有什么概念,但她特别在乎乡邻对她后人品质的评价。
母亲共生养了五儿一女。子女众多,决定了我们家长期走不出贫困的影子。至今我都无法想象在那个饥饿的年代,父亲和母亲是怎么带我们一大家人熬过来的。萝卜、红苕、土豆、南瓜是主粮,大米、麦面只能零星掺杂其中,每年最难过的是正二三月,各种可以入口的嫩绿树叶也经常充当口粮。俗话讲,“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母亲的精细安排,让一大家子一年一年艰难地捱过来了。父亲爱交友,家里总是人客不断。我们平时难得吃上一次肉,可客人来了,母亲总是变戏法似的端出一两个荤菜。面对我们的狐疑,母亲总是说,家里再穷,可面上的事情总要撑圆,你们老汉在外头的面子总要维护。有一次家里来了七八个客人,我留意到母亲与客人寒喧几句后,轻手轻脚地从灶屋后门出去,到隔壁朱家大娘家借了一块腊肉和几个鸡蛋。在那个饥饿年代,一年四季都有从外地逃荒的妇女来到山寨乞讨。每来一拨人,听她们讲其家乡的惨况,母亲都会陪着流一把伤心泪,然后给每人煮上冒冒一碗面条,临走时还要给人家一些粮食,有时是大米,有时是麦子,哪怕是碗豆、胡豆,也要给人装上一小口袋。一个腊月天,快到年关了,我们家里来了一位安徽的逃荒客,母亲吩咐我去印一升米。我见家里米缸只有半缸米,便只印了半升米,并抱怨道,只晓得对别人大方,就不想我们过不过年了。母亲轻声叱了我句“小气”,转身到米缸装了满满一升米。待安徽妇人走后,母亲板着脸对我教育道,四儿啊,别人拿着这升米是回去救命的,我们缺了这升米不会饿死人。人这一辈子,总会有三灾八难的,救了别人的急,才会有人救你的急。
母亲作为一个典型的农村妇女,大字不识,却期望子女能成为读书人。大哥、二哥、姐姐大我们很多,由于时代的原因,没有念过几年书便早早成了家。三哥考上了高中,却念及我和弟弟年幼,家中负担太重,中途辍学到新疆当兵去了。母亲对我们兄弟没有更高的期盼,她只希望我们成为“周先生”那样的人。周先生是老家的一名老中医,出生书香世家,是民国时期的大学生。周先生医技高超,为人儒雅随和,对世事宠辱不惊。由于周先生家庭成分的原因,在一些运动来临的时候会受批斗。批斗中,任人辱骂从不分辩,批斗一结束,周先生把脸一洗,照样挎着药箱下乡巡诊。母亲像绝大多数乡亲一样,对周先生特别尊重,要求我们学习周先生那种“拿得起放得下”的大气,她认为只有真正的读书人才做得到这一点。我从初中醒事,开始发奋读书,无论上下学路上,还是坡上放牛,都是手不离书本。每当周末,我和弟弟在老屋后的井台边读书写作业,母亲都会放下忙碌的庄稼活计,拿上针线,很享受地陪着我们。我想,当时她那双眼睛里面不知盛着多长多远的期望。还好,我后来如愿考上了北方的一所大学,弟弟考上了南京的一所军事院校。但我们些微的成就,是父母十数年的辛劳铺就的,是他们用一生的健康作为代价换来的。我大学毕业时,一位长辈意味深长地对我说,老四呀,你这大学是你母亲一棵棵菜一捆捆葱卖出来的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还没有兴起打工潮,农村地区虽然解决了温饱问题,但用钱还是非常紧张。靠卖粮也卖不到几个钱,父亲也做不来生意,我们的学费和每个月的生活费就靠母亲卖地里的小菜来凑。老家乡场小,场镇居住人口少,卖菜卖葱得来的全是角角票分分钱。有一个学期交5元住宿费,管生活的老师接过我一大把角票,还没数完,就不耐烦地扔在地上,骂骂咧咧嘴上还带了一个脏字。我气得当场从地上抓了块砖头,朝生活老师冲去。在同学们的喝阻下,手中的砖头最终没有拍向生活老师。母亲长期教育我,人生只记恩莫记仇,但几十年来我几乎没有回过那所初中学校,那位生活老师对我留下的心灵创伤太深,他侮辱的不是我,而是我的母亲,侮辱的是一位母亲对孩子的期望和深爱。
老屋前曾有两棵百年柿子树,每年成熟时,母亲就将柿子摘下来,浸浮在两个巨大的瓦缸里,一周过后脆甜脆甜的,口感非常好。我们全家人都没有口福,所有柿子都被母亲背到乡场上卖了,变成了我们的书学费和生活费。每年腊月三十天午饭前,母亲都会带着我们兄弟,端上一碗米饭,在树腰切开一个口子,并往口子里喂满米粒。母亲说,这两棵柿子树于我们家有恩,我们过年了也得让它们过年。说来也怪,那些年柿子树总是枝繁叶茂,硕果累累。前几年,这两棵百年老树树干皲裂,再也不发新叶再也不结果了。因为修路,老树被砍伐时,母亲抹着眼泪说,树哇,就像我们人一样,老了就没多大用了。
也许是生活的压力,父亲和母亲老是争吵,父亲总是强势,母亲总是弱势。到了晚年,尽管后人们都很争气,日子也比较富足,他们仍然争吵,母亲变得强势,父亲处于守势。母亲总是将几十年的生活琐事拿出来讲,向我们“控诉”父亲当年如何如何欺负她,父亲觉得理亏,就总是不还嘴,到了最后父亲总是把酒壶拿出来,摆上两个杯子,说句“好了,不说了,喝酒”。老俩口的晚年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重复着。父亲一生好酒,母亲本是滴酒不沾的,到了晚年陪父亲喝酒,喝着喝着也就喝上了瘾。儿孙们从外面带回来的好酒,他们一概不喝,只喝老家乡场上那家老酒厂的高粱酒,早中晚三顿,顿顿不能缺酒。母亲是去年正月初五离开人世的,生命弥留之际已经是无法进食。虽然儿孙环伺床前,但父亲坚持一直守在母亲身边,手端着酒壶,隔一阵子就给母亲喂一小口酒,隔一阵子就给母亲喂一小口酒。母亲走的那一刻,一家老小哭成一团,老父亲痴痴地望着母亲的遗体,手中酒壶溢出的酒,洒了母亲一脸。
老母亲走后,我再也没做过困扰我几十年的那个冰原噩梦了。
我这才明白,我再也没有母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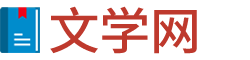 返回首页
返回首页